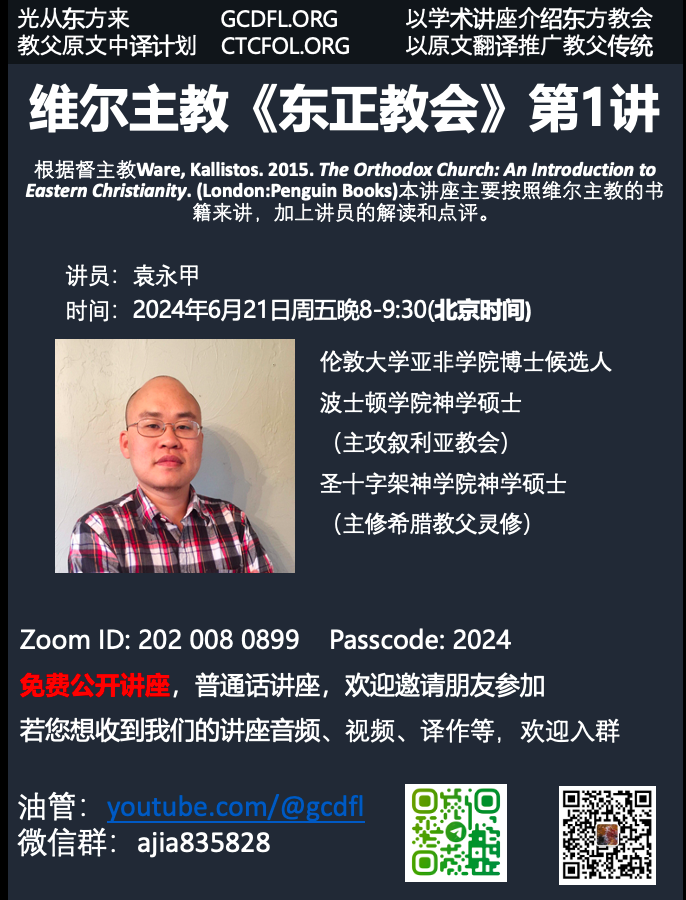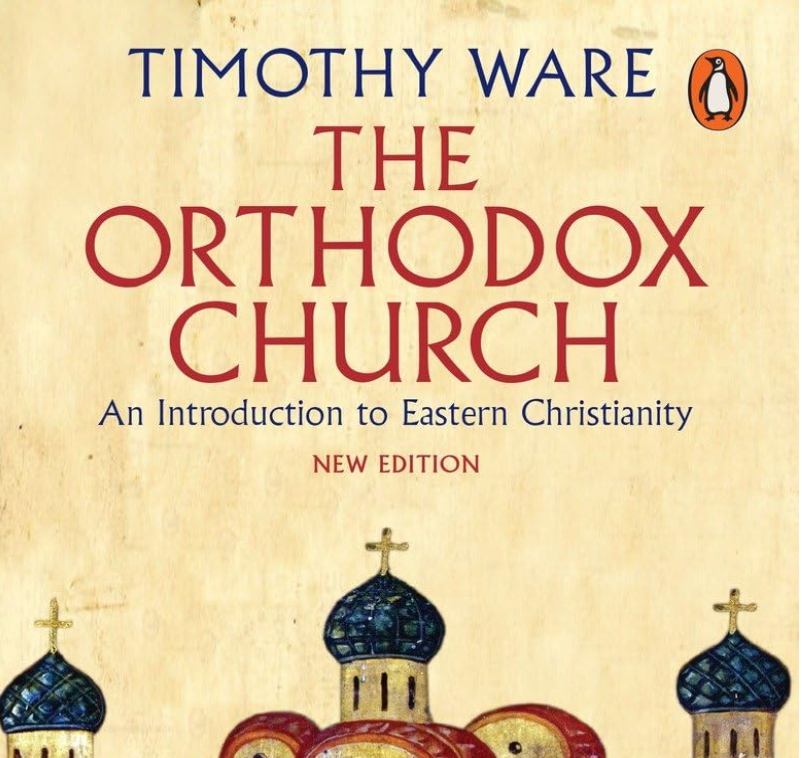
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3课 20世纪散居的东正教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3课 20世纪散居的东正教。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1月24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斯斯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9章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第九章 二十世紀之三:流徙和使命 所有異鄉都是我們的祖國,所有祖國都是異鄉。——《丢格那妥書信》5:5 一、合一的多樣性 從文化和地理的觀點而言,過去的正教幾乎只是作為一個「東方的」教會出現·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様。正教徒廣泛「散佈」於傳統的正教國家疆域以外,其主要中心是北美,但是世界的每個部分都有分支。論人數和影響力,希臘人和俄羅斯人佔據主導地位,但是流徙絕不僅僅限於他們,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及其他人都擁有一席之地。 正教徒的流徙始於很早以前。倫敦的第一個希臘教會早在一六七七年開放,位於當時時髦的蘇荷(SOHO)區。它的生涯短暫而不順利,在一六八二年被關閉。倫敦的聖公會主教康普頓(Henry Compton)禁止希臘人在教堂中擁有聖像,要求他們的神職人員略掉所有聖徒禱告,不承認耶路撒冷會議(1672年),拒絕「變質説」教義。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向英國大使芬奇(John Finch)爵士抗議這些情況時,後者反駁,「在英國的公共教堂表達羅馬的信仰是不合法的,表達希臘信仰同表達羅馬信仰一樣不合法。」1 在倫敦建立的第二個正教崇拜地點是俄羅斯大使館教堂,它在一七二一年左右開放,享有外交豁免權,所以英國的聖公會主教不會注意裏面發生甚麼。在十八世紀使用這個教堂的是希臘人丶英國皈依者和俄羅斯人。希臘人於一八三八年能夠在倫敦開辦一所他們自己的教堂,聖公會領導者沒有做出任何刁難限制。 正教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出現在北美大陸·俄羅斯探險家白令(Bering)和奇里科夫(Chirikov)於一七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發現阿拉斯加海岸,在五天後的先知伊利亞節上,美 洲的首次正教禮儀於停泊在錫特卡(Sitka)灣的聖彼得號輪船的甲板上舉行。數年以後,一大群希臘人到達佛羅里達,建立了新士麥那(New Smyrna)殖民地,但是這個冒險遭到了災難性的失敗。2 如果説正教徒流徙的事實本身不是新出現的,那也只是在二十世紀,流徙才達到使正教成為非正教國家宗教生活重要因素的程度。即使在今天,由於民族和管轄上的分隔,流徙的影響力比它本應發揮的作用要小。 在流徙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它使一百多萬人被流放,其中包括國家的文化和知識精英。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包括希臘人和斯拉夫人在内的正教徒移民,大多數都是很少受教育的穷人——尋找土地或工作的農民或手工勞動者。但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流放大潮中,許多人具備在學術層面上與西方接觸的能力,能夠以大多數先前移民顯然不能的方式,將正教展現給非正教世界。在一九一七年後,特别是最初的幾年,俄羅斯移民有驚人的成果:據計算,有一萬本書籍和兩百份期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間出版,這還不包括學術和科學評論。今天的西方,特别是美國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希臘人,在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學術和專業領域發揮着卓越的作用。 從宗教方面來説,正教徒移民按照強烈的民族劃分被組織起來。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最初的主動權不是來自上層,而是來自下層:來自平信徒而不是高級神職人員。 一群移民聚齊起來並邀請一位來自故國的神父,一個教區就形成了。在很久以後,主教才直接參與這種安排活動。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説,當地的教區教會是他們同祖國的重要紐帶,他們在這聽到自己的母語,這是他們民族風俗的方舟和衛士。因此西方的正教自開始時就具有明顯的種族特徵,其原因完全可以理解。 民族現在是上帝的禮物。索爾仁尼琴在一九七0年的諾貝爾獲獎演説中正確地指出:「民族是人類的財富,它的集體個性;其中最微小的部分都有其自己的特殊顏色具有神聖含義的特殊方面。」3 不幸的是,在流徙的宗教生活中,民族忠誠本身是合法的,它的勝利以犧牲正教的大公性為代價,這導致教會結構發生嚴重的碎片化。每個地方不是只有一個由一位主教管轄的主教教區,西方幾乎到處都發展起多重平行的管轄權,每個主要城市都同時有幾位正教主教。無論這種情況的歷史原因是甚麼,它肯定同正教的教會觀念相悖,普世宗主教迪米特里奧斯在一九九0年訪問美國時,正確地把美國正教的種族分離稱為「真正的醜聞」。今天,我們許多人都期望看到,在所有西方國家裏,一個地方教會以統一的組織方式接納所有正教徒;單個教區如果有意願就能夠保持其種族特徵,但是所有人都要承認同一地區的高級神職人員,每個國家的所有高級神職人員要在會議上共同就坐。遺憾的是,這僅僅是一個遙遠的期望。目前的情況,要超越種族分離是困難的。 除了這些種族分離,許多民族團體內部也有分裂,從屬靈方面説,它對西方正教生活的傷害比種族分離更大。除了一些緊張的地區以外,希臘移民的教會組織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就或多或少聯合起來,歸於普世宗主教區之下。但是逃離共產主義的正教徒幾乎都分裂成相爭的派,一派維持同母教會的聯繫,另一派建立獨立的「流放教會」。儘管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垮台了,但是大多數教派分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俄羅斯人流徙的故事特別複雜和悲慘。下面是四個主要的管轄區: (一)莫斯科宗主教區,包括那些選擇同俄羅斯的教會權威維持直接聯繫的移民教區(?三萬至四萬會員,在西方各處)。 (二)俄羅斯以外的俄羅斯正教會(ROCOR);也被稱為「俄羅斯正教流放教會」、「國外的俄羅斯正教會」、「會議教會」、「卡爾洛夫茲(Karlovtsy)會議」(大約有十五萬會員)。現在的領導者是都主教維塔利(Vitaly,1986年當選)。 (三)西欧的俄羅斯正教主教大管區,受普世宗主教區管轄,也被稱為「巴黎管轄區」(大約有五萬會員)。現在的領導者是賽吉烏斯大主教(1993年當選)。 (四)美洲的俄羅斯正教希臘天主教會,也被稱為The Metropolia它在一九七0年成為「美洲正教會」(美國正教會[OCA],會員總數為一百萬)。現在的領導者是都主教迪奥多西(1977年當選)。 這種分離是怎樣出现的?莫斯科宗主教吉洪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日發佈一項命令,向不能同宗主教區維持正式關係的俄羅斯教會主教授權,准予他們建立自己的臨時性獨立組織。被流放的俄羅斯主教在白軍潰敗以後決定執行這項命令,而吉洪是否想要在俄羅斯疆域以外執行這項政策卻是個問題。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二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在塞爾維亞宗主教迪米特里捷(Dimitrije)的支持下,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在南斯拉夫的斯雷姆斯基卡爾洛夫奇(Sremski-Karlovci-[Karlovtsy])召開。一個管理俄羅斯流放正教徒的臨時組織建立起來,它位於主教會議之下,主教會議每年在卡爾洛夫茲召開。卡爾洛夫茲會議的首位領導者是曾任基輔都主教的安東尼( Antony[Khrapovitsky],1863-1936),在當時的俄羅斯高級神職人員中,他是最勇敢和最有原創性的神學家之一。一九二一年的卡爾洛夫茲會議做出一些決定,還通過一項違背許多參會者意願的提議恢復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 卡爾洛夫茲主教們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態度使吉洪處於一個微妙的境地。他於一九二二年下令解散會議,但主教們在實質上以相同的方式重新召開會議。卡爾洛夫茲主教完全拒絕宗主教權的「監護人」塞吉烏斯都主教一九二七年的聲明。而塞吉烏斯一方則在一九二八年宣佈卡爾洛夫茲會議的一切規定都是無效和無用的。會議總部在二戰後移到慕尼黑。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就移到紐約· ROCOR於一九九0年將其工作擴展到前蘇聯,在那祝聖兩位主教,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各地建立教區; ROCOR的俄羅斯分部被稱為「自由俄羅斯正教會」。這一舉動顯然導致 ROCOR和莫斯科宗主教區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 ROCOR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以來逐漸被孤立,儘管它仍然同塞爾維亞教會維持着聯繫。這種分離狀態在很大程度上由於 ROCOR自己的選擇:領導者強烈地感受到,其他正教會由於參與普世運動而危及了真正的信仰。無論出於甚麼原因, ROCOR的孤立必定是很大的遺憾。它忠誠地保存了正教俄羅斯的禁慾丶修道和禮儀傳統,這一傳統靈性是西方正教徒極其需要的。 所有被流放的俄羅斯主教起初試圖同卡爾洛夫茲會議合作,但是分裂在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現,這導致上面提到的第三個和第四個組織建立了。巴黎管轄區源於巴黎的俄羅斯主教伊弗洛基都主教(1864-1946),吉洪宗主教已經任命伊弗洛基為他在西歐的主教。伊弗洛基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同卡爾洛夫茲會議決裂,在一九三0年被宗主教權的監護人塞吉鳥斯否定,因為他代表蘇聯被壓迫的基督徒,參與倫敦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禱吿儀式。伊弗洛基在一九三一年向普世宗主教弗提烏斯二世求助,後者接納了他和他的教區,將之置於君士坦丁堡的管轄之下。伊弗洛基在一九四五年死前不久重返莫斯科管轄區,但是他的絕大部分信眾選擇繼續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管轄。儘管巴黎的俄羅斯大主教轄區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間遇到很多困難,但至今仍然接受普世教權的管轄。 第四個組織是北美 Metropoliao·美洲的俄羅斯人在革命後的處境同其他地方的因俄國革命造成的移民有點不同,因為在俄羅斯以外的國家中,唯有這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有常設的,帶有居住主教的俄羅斯主教教區。紐約的都主教普拉(Platon,1866-1934)同伊弗洛基一样,在一九二六年脱離了卡爾洛夫茲會議;一九二四年,他就已經斷絕了同莫斯科宗主教區的聯繫,因此在一九二六年以後,美國的俄羅斯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組織。在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六年間, Metropolia維持同卡爾洛夫兹會議的聯繫,但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克利夫蘭(Cleveland)會議上,大多數代表投票重新歸屬莫斯科宗主教區管轄,條件是莫斯科允許他們維持「現在這樣的完全自治」。宗主教區在那時不能同意這點。但是俄羅斯教會在一九七0年不僅允許Metropolia自治,而且允許Metropolia獨立。這個「獨立的美國正教會」 (OCA)已經得到保加利亞、格魯吉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教會的承認,但是還未得到君士坦丁堡或任何其他正教會的承認。普世宗主教區認為它同其他正教會協商行動,自己有權在美國建立獨立教會。儘管爭端尚未解決,但OCA繼續同其餘的正教會維持充分的聯絡。 二、西方的正教 我們不是要面面俱到,而是簡要地概覽西歐、北美和(更簡要地概覽)澳大利亞的正教。巴黎是西歐的主要知識和靈性中心。一九二五年在這裏建立了著名的聖塞吉烏斯神學研究院(受俄羅斯人的巴黎管轄區管轄) ,它發揮了連接正教徒和非正教徒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時期,研究院的教授中湧現出一批特別傑出的學者。聖塞吉烏斯神學研究院以前的在職者中包括曾擔任第一任院長的主神父布爾加科夫(Sergius Bulgakov, 1871—1944) ;任第二任院長的主教卡西安(Cassian, 1892-1965) ;卡塔舍夫(Anton Kartashev, 1875- 1960) ;費多托夫(George P, Fedoto, 1886—1951);伊多科莫夫(Paul Evdokimov, 1901—1970) 。現有教授安德羅尼科夫( Constantin Andronikoff) 、鲍瑞斯科伊神父(Boris Bobrinskoy)和法國正教作家克莱蒙特(Olivier Clement)...